摘要
传统的功利主义聚合(utilitarian aggregation)将心智视为可以累加福利的离散个体。但当我们摒弃二元论时,我们会发现心智并非独立单元,而是模糊地融合成一个整体。此外,大的心智可以由许多小的心智组成,每个小心智都有自己的个体意识。我提出了几个修正功利主义加总的方法以应对这一困难,但似乎都不太有希望。目前,我继续使用传统的、权宜之计的方法,即在每个显著的组织层级上区分最显著的子系统。模糊、嵌套的对象/实体问题不仅困扰功利主义,也困扰许多其他形式的后果主义。
目录
引言
杰里米·边沁的功利主义基于"每个人都算作一个"的原则。福利经济学同样聚合个人的偏好。但什么是个人?
传统西方思想认为每个人和有知觉的动物都有一个单一、离散的灵魂或统一的意识。个人则是一个被灵魂或统一的体验主体所寄居的单元。
但丹尼尔·丹尼特对意识的看法消除了笛卡尔剧场——一个所有意识发生的单一场所。相反,意识是分布式的,不同事件在不同地点和时间发生并相互作用,产生我们最终称之为意识流的东西。心智边界变得模糊,因为在行为者和其环境之间没有原则性的分离。
此外,小心智可能结合形成更大的心智,而这些又可以结合形成更大的心智。因此,心智不再是互不相交的。下一节将详细阐述这个问题出现的一些情况。
嵌套心智的例子
Burd、Gregory和Kerbeshian讨论了脑组织培养,并询问何时一团神经组织复杂到足以构成"一个人"。如果精神生活出现在比整个大脑更小的组织簇中,那么我们的头骨可能包含几个"心智"。事实上,我们可以在分裂脑患者身上看到这一点。
我们的大脑由许多子过程构建而成,其中一些可能足够复杂和独立,值得被视为它们自己的小心智(在丹尼特的术语中称为"恶魔")。全局工作空间理论(GWT)谈到了低级组件的"联盟",它们竞争注意力。GWT通常将这些子过程称为"无意识的",只将全局信息的传播确认为"有意识的",但这种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分离是人为的。
对于功能主义者来说,嵌套心智最明显的例子之一是中国大脑思想实验,在这个实验中,中国人口通过电话通信等方式实现正确组织的功能过程,创造出一个集体心智。中国公民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突然变得无意识,所以结果显然(至少)是两层意识,一层嵌套在另一层之中。
我在其他地方讨论过中国大脑和相关的思想实验:
功利主义聚合的困难
乍看之下,嵌套心智似乎对功利主义聚合构成不大的问题:我们可以计算所有中国公民,然后再计算他们的集体大脑(可能使用与普通人不同的道德权重)。如果嵌套心智总是像这样清晰分离,这种程序就可以很好地工作。但实际上,"心智边界并不总是清晰的"。如果整个中国是一个大脑,如果我们忽略一个随机的中国人,他的信息处理并不那么重要,会怎样?"中国减去一个人"是否也构成另一个集体心智?除了完整的中国心智外,它是否应该拥有自己的伦理权重?
Eric Schwitzgebel认为"如果唯物主义是真的,美国可能是有意识的"。但如果整个美国都有意识,那么每个州呢?每个城市呢?每条街道呢?每个家庭呢?每个家庭呢?当新的政府部门成立时,是否会创造一个新的有意识实体?公司合并是否会减少有意识实体的数量?这些似乎是愚蠢的问题——事实上,它们确实是!但当我们试图将世界划分为独立、离散的心智时,这些问题就会出现。最终,正如人们所说,"我们都是相互联系的"。个体化边界是人为的,不追踪任何本体论或现象学上的基本东西(除了可能在基本物理粒子和结构的层面上)。行为者与其环境之间的区别只是我们为某些目的在物理学的一团中画出的边缘。
我自己的观点是,宇宙的每个子系统在某种程度上和某种方式上都可以被视为有意识的(功能主义泛心论)。在这种情况下,哪些系统算作聚合的个体的问题变得最为棘手,因为似乎我们可能需要计算宇宙中的所有子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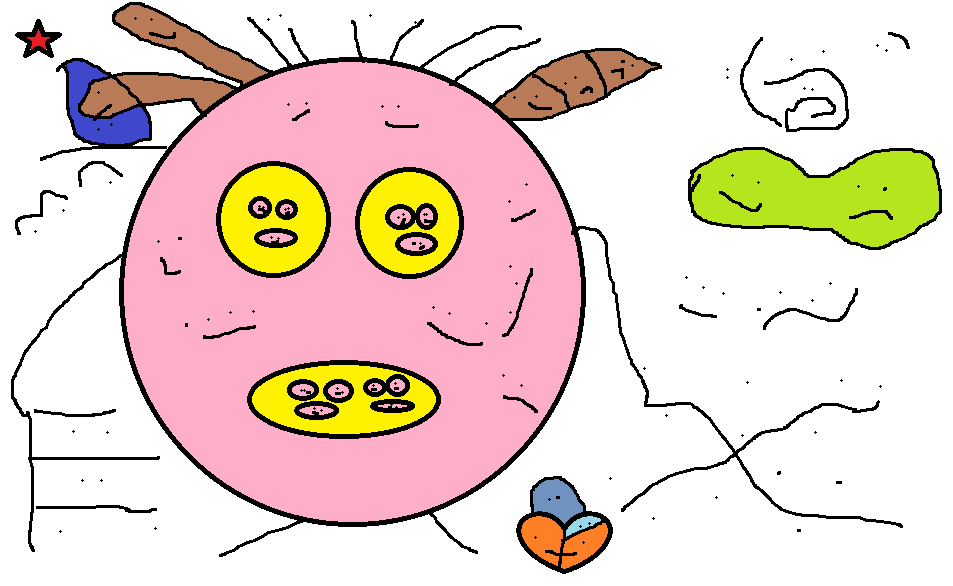
可能的解决方案
对所有充分个体化的"对象"求和
聚合问题的标准方法相当粗糙:
- 区分看似不同的计算组织层级(例如,中国公民是一个层级,集体大脑是另一个层级)。
- 在每个层级上,将看似相对统一的系统区分为不同的个体(例如,区分每个中国人与其他中国人)。
- 根据每个个体的感知程度给予权重。
- 对所有组织层级的所有个体求和。
这个方法对设想的抽象层数(步骤1)和什么东西算作个体化对象的人为边界(步骤2)这些问题并没有充分考虑。例如,也许动物的每个细胞都算数,动物的每个器官也算数。细胞对也算数吗?单个肌肉纤维是否除了整个肌肉之外还要单独计算?心脏的每个腔室是否除了整个心脏之外还要单独计算?皮肤的每一层是否除了整个皮肤之外还要单独计算?每个肺还是只算一对肺?每个大陆还是只算整个地球?作用于物体的每种力还是只算它们的总和?每个子程序还是只算整个程序?
功利主义聚合的问题出现是因为心智既模糊又嵌套。个体化对象的方法试图消除心智的模糊性,但仍允许它们嵌套。下面讨论的下一个提议则旨在消除心智的嵌套性,因为如果心智必须是不相交的,那么可能的心智数量就会大大减少。
只计算最小或最大尺度
我们可以尝试对最小的系统求和,忽略更大的系统。例如,只对单个中国人求和,忽略他们的集体大脑。但这是错误的,因为集体大脑有一种不同于每个中国人的意识。
相反的方法是计算集体大脑并忽略单个中国公民,但这同样是错误的,因为中国公民并不会因为实现了集体大脑就失去意识。(Schwitzgebel在他的论文的"反嵌套原则"部分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还要注意,实际上,最小层级的心智不是单个中国人,而可能是他们大脑中的子系统、单个神经元、单个原子,甚至单个超弦。而最大的有意识心智不仅仅是中国,而是整个多元宇宙。
对所有系统求和
一种暴力方法可能是对所有系统求和,即整个宇宙的所有子集!这会使功利主义分析的计算复杂性呈指数级增长,因为给定一个大小为N的集合,其幂集的大小为2N。例如,如果我们仅限于可观测宇宙,并仅以原子作为基本构建块,~1080个氢原子将意味着这个宇宙中有~21080个子系统。
计算宇宙中不相连的子集也似乎很奇怪——例如,一个由我大脑的一半和地球另一端某人大脑的一半组成的系统。
对所有时空连接的系统求和
也许我们可以将自己限制在时空连接的宇宙子集上。但即便如此,系统集合仍然是巨大的。
计算所有连接的子集也保留了很多冗余。例如,有一个由我的身体组成的系统,但也有一个由我的身体加上我额头前一立方厘米空气组成的系统,还有一个由我的身体加上我左小指前梯形区域的空气组成的系统,以及天文数字般多的此类排列。这些大多数代表大致相同的有意识个体,因为空气分子对系统的贡献是最小的。直觉上,这些应该都折叠成系统最重要的部分,否则包含微不足道的空气分子的系统在功利主义计算中的权重应该大大降低。
意识模板
功利主义个体化是一个两步过程:首先识别看似相对统一的系统,然后评估它们的意识程度。也许我们可以将这两个步骤结合起来。也就是说:
- 考虑每种意识类型——例如,特定类型的幸福、特定类型的恐惧、以特定方式看到蓝色。每种涉及什么样的功能处理"模板"?
- 考虑宇宙的所有子集,尝试将该模板与该子集进行模式匹配。
- 将实现模板的最小可能宇宙子集视为个体。所以,例如,如果一个模板是我的身体,那么这种方法会忽略笑话系统"(我的身体)+(我面前的空气分子)",因为那不是模板的最小实例。
- 最终得到每个模板的最佳匹配系统列表。对这些进行聚合。(或者,测量每个可能系统与模板的匹配程度,并对每个可能系统进行加权求和。)
这种方法看起来有些前景,尽管对于非狭隘的意识观点来说,模板的数量可能天文数字般高——在极限情况下,可能与宇宙子集的数量一样高。我们可能会识别一些我们认为构成现象体验的关键过程,并只使用这些。事实上,许多意识理论就是这样做的。但有一个风险是会遗漏大量道德相关的计算。
话虽如此,大量模板的问题也困扰着其他个体化方法,因为它们也需要评估每个系统的意识程度。
完全放弃个体化
圣杯将是完全避免看宇宙的子集——如果我们能以符合我们直觉的方式做到这一点。但我们如此习惯于以个体化的方式思考,以至于我们的直觉可能会反对非个体化的方法。个体化对于评估效用函数也很重要,因为效用函数源于统一的、个体化的物理过程的偏好。
有一些放弃个体化的琐碎方法。例如,我们可以简单地对宇宙的基本粒子总数、总动能或其他一些物理量求和。但很难看出这与伦理有什么直接关系。
最终,我们想要一些更复杂的函数,以不将宇宙分解为子集的方式将宇宙映射到(不)效用。对于任何福利主义价值理论来说,这可能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福利似乎需要评估个体系统的感受和偏好。
其他后果主义也面临嵌套问题
功利主义并不孤单;个体化和聚合问题也困扰着大多数其他形式的后果主义。
例如,一个回形针最大化者可能会在大回形针里塞小回形针。如果你考虑一个回形针去掉两端的子集呢?那肯定也能夹住纸吧?回形针内部的圆柱形环呢?那也有回形针的形状。由回形针加上它上面的灰尘组成的系统呢?或者回形针加上它所在桌子的几个分子?衣架是回形针吗?两个人的手指呢?三个人的手指呢?放在纸两端的两块磁铁呢?用于此目的的许多小磁铁呢?只要纸的每一边至少有一个磁铁,小磁铁的任何子集都是回形针吗?什么算作纸呢?几根植物纤维就够了吗?在这种情况下,树是回形针吗?树的每个年轮也是回形针吗?围绕树的空气分子呢?围绕地球的外太空呢?
再举一个例子,假设我们想要最大化爱。爱这个复杂概念包括许多组成部分,如(1)吸引力,(2)做好事,(3)能量水平提高等。这些琐碎的实例可以在整个宇宙中看到,比如(1)当磁铁相互吸引时,(2)当阳光温暖寒冷的动物时,(3)当风转动风车时。爱也可以嵌套,比如电子被质子吸引(第1层),在两个最近加强突触的神经元之一内(第2层),在一个恋爱中的人的大脑内(第3层),在一个最近加强与盟友关系的国家内(第4层),在一个继续被太阳吸引的行星内(第5层),等等。
除非施加极其精确的价值规范,否则后果主义聚合会变得极其复杂。但大多数后果主义价值——幸福、爱、公平、知识等——本质上是模糊的,如果同时精确和简洁地形式化,就无法满足我们期望的含义。
结论
我不知道正确的答案。我希望标准的、权宜之计的方法,即在最显著的组织层级内进行个体化,可以作为我经过进一步反思后最终认可的更优雅方法的足够好的近似。
目前进行任何精确计算似乎都是不可行的,但我们可能仍然可以对一般原则进行粗略估计。例如,如果动物般的行为者似乎比其他类型的系统有意识得多,我们可以主要集中评估我们的行为如何影响动物般的行为者。
但从长远来看,我们最好的办法是将这些问题交给未来几代人。我们现在能做的是将未来推向更好的方向,为我们更聪明的后代进一步探索这些难题奠定基础。
也许我们的后代会拒绝我们的整个方法,认为这是试图修补本质上混乱的个人体验道德概念的误导尝试。但我非常强烈地感觉到,例如,常识中的动物痛苦实例是可怕的;一个过于抽象的方法可能会忽视这一事实。所以我不确定我会在多大程度上将功利主义聚合的彻底改革视为道德进步还是对我价值观的腐蚀。
致谢
这些想法中的一些可能受到了Caspar Oesterheld的"在物理世界模型中形式化偏好功利主义"早期草稿的影响。Jonah Sinick和David Pearce也帮助启发了本文的部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