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列举了几个原因,说明我为什么不优先考虑生物相关技术作为减少痛苦的策略。生物似乎很可能在几个世纪内被机器取代,即使不是这样,影响未来的政治/社会轨迹可能比推动许多富人出于自私原因已经想要的相对拥挤的技术发展更重要。不幸的是,我预计高科技解决方案帮助野生动物的可能性不如仅仅通过扩大那些已经产生这种效果的人类活动来减少野生动物数量。话虽如此,推广一个普遍的减少痛苦的运动似乎相当有价值。
目录
引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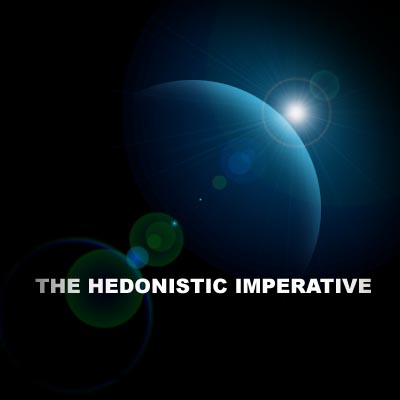 David Pearce的快乐主义命令对我的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本书是导致我将痛苦视为最重要的利他主义优先事项的关键因素之一。然而,在实践层面上,我减少痛苦的方法往往与Pearce阐述的技术愿景几乎没有联系,比如改进药物、基因工程、大脑研究以及生物/纳米/信息技术等。我将这些技术方法称为"快乐主义命令"项目(HI),为了与Pearce的在线书籍区分开来,这里不使用斜体。
David Pearce的快乐主义命令对我的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本书是导致我将痛苦视为最重要的利他主义优先事项的关键因素之一。然而,在实践层面上,我减少痛苦的方法往往与Pearce阐述的技术愿景几乎没有联系,比如改进药物、基因工程、大脑研究以及生物/纳米/信息技术等。我将这些技术方法称为"快乐主义命令"项目(HI),为了与Pearce的在线书籍区分开来,这里不使用斜体。
虽然我没有详细分析HI的提议,但我通常怀疑减少生物痛苦的技术并不是集中资源的最佳地方,原因有几个,我将在本文的其余部分讨论这些原因。
注:对Pearce观点的任何误解都是我的错;我最后一次阅读快乐主义命令是在2006年。而且本文只是表达友好的认识分歧。作为一个朋友和有远见的人,我非常钦佩Pearce,只希望他的工作一切顺利。
远期考虑
我不优先考虑HI的最重要原因是,我预计生物生命不会再存在超过几百年,因为生物很可能被机器智能取代。如果文明停滞或崩溃,情况可能不是这样,但这些情况的后果不如机器智能发展并殖民太空的情况重要,后者会天文数字般地增加痛苦。此外,如果文明永久崩溃,我们很难有资源或动力在整个生物圈推广HI技术。
机器痛苦
减少机器痛苦的方法看起来会与减少生物痛苦的方法大不相同。无论如何,未来几代机器智能可以解决减少痛苦的细节问题——如果(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它们足够关心痛苦的话。在我看来,改善我们的机器后代的价值观并防止该领域最坏情况的未来动态,似乎比研究生物技术更重要。
当然,Pearce怀疑数字计算机是否会有意识。即使相信这一点,人们也应该对数字意识保持一定的概率,考虑到未来可能存在比生物意识多得多的机器意识,机器意识可能的情况在期望值计算中可能仍然占主导地位。但假设一个人非常确信生物将永远是痛苦的主要来源。即便如此,我仍然怀疑废奴主义技术是否是最重要的关注领域,因为我认为引导未来的价值观和权力动态可能更重要,下面将讨论这一点。
影响权力动态很重要
即使许多怀疑机器意识的人也承认机器可能会继承地球。即使智人确实保持了权力的缰绳,远未来的价值观可能与我们的价值观大不相同。如果不加以控制,进化力量可能会侵蚀我们现在这种充满副产品的价值观,即使当前的价值观保持不变,社会也可能不可阻挡地朝着大多数人类不赞成的方向发展。
即使我们开发出让人们沉浸在幸福梯度中的技术,这些技术也不一定会永远使用。如果痛苦的心理状态能带来任何竞争优势(很可能如此,因为进化产生了幸福和痛苦,而不是幸福的梯度),那些保留痛苦的人可能在经济和进化上有优势。除非我们创造一个全球单体来阻止进化军备竞赛,否则我们的理想很可能会被竞争压力所压倒。
换句话说,我认为影响未来的方向盘可能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重点。这可能意味着影响通用人工智能的发展,或影响政治/社会轨迹,或传播以减少痛苦为中心的价值观。它也可能意味着推动有益的技术,但主要是着眼于这些技术如何塑造未来的权力动态。我不清楚提高幸福感的技术是否会让减少痛苦的价值观对人类的未来有更多控制,尽管我愿意听听这种观点的论证。
加速技术可能是坏事
HI研究经常涉及推进神经科学和其他科学/技术前沿。但加速技术的净影响通常并不明显,而且可能是负面的。例如,加速神经科学可能会加快强大机器智能的发展,也可能增强人类创造有知觉的数字生命的能力,其中一些将遭受重大痛苦。
生物技术的进步也可能增加灾难性风险,这从减少痛苦的角度来看是一个复杂的话题。
痛苦和同理心
经历抑郁或重大生活痛苦的经历与关注减少痛苦之间可能存在相关性,尽管我希望这个话题能得到更严格的探讨。如果从未面对过抑郁的人平均来说对他人的困境不那么同情,HI会不会减少对非人类和远未来生命的痛苦的同情心?或者可能恰恰相反——那些情感生活更丰富的人更倾向于同情。也许专注于建立同理心的HI技术可以克服这个担忧。
短期考虑
我自己的努力并不完全集中在机器智能的远未来。我也投入了大量资源来减少短期内野生动物的痛苦,部分是出于情感"模糊"的原因,部分是出于其他启发式原因。但即使在短期减少痛苦方面,我认为其他干预措施比HI更有前景,原因如下。
以人为中心的HI不是一个被忽视的领域
纵观历史,大多数人都致力于减少痛苦和改善幸福感。当然,现代技术方法还没有被广泛追求,新的突破正等待着我们。尽管如此,这个领域似乎并不太被忽视,因为许多富裕国家的人愿意为享乐改善付费。例如,我们对抑郁症和其他情绪障碍的治疗进行了大量研究。如果改进相对容易发现,制药公司和其他机构肯定早就跳上这个机会了。
在某些情况下,非理性或寻租的政治限制可能会抑制研究,比如对迷幻药的研究。但游说改变这些规则会遇到强烈的反对,似乎不太可能是低垂的果实。
未来的设计婴儿可能会在改善富人的幸福感方面取得巨大进展,但这种发展似乎也很可能会被精英阶层的自身利益推动,而且在政治上是一个拥挤的问题。此外,设计婴儿对远未来的整体影响远非明确,因为更聪明的人会加速有害技术和有益技术的发展。
以动物为中心的HI似乎很困难
人类只占地球上动物的一小部分,甚至只占所有动物神经元的一小部分。减少短期痛苦时最重要的关注点可能是动物,它们不仅比人类数量更多,而且生活往往更糟糕。
很少有人在研究动物的HI技术,尽管也许一些人类HI的发现可以应用于各个物种。虽然动物为中心的HI研究可能看起来是一个被忽视的原因,但我怀疑它有多大前景,因为很难说服人们为帮助动物而承担成本。我们甚至无法在2016年说服政府取缔工厂化养殖或要求更人道的屠宰方法。很难想象我们会看到对动物,特别是野生动物的享乐改善进行大规模昂贵研究的投资。人类就是不那么富有同情心,在生物动物在这个星球上还剩下一两个世纪被机器取代之前,社会态度不会改变太多。也许一些富有的"动物慈善家"(为非人类动物做慈善的人)会开发和传播一些HI改进措施给动物,但这些可能只会在小规模进行或只影响少数物种。
我在这篇关于基因驱动的文章中表达了类似的对动物HI的悲观看法。考虑到人们对是否应该使用基因驱动来消除或重新设计一种昆虫(蚊子)以每年拯救超过一百万人类生命还存在争议,似乎几乎无法想象人们会考虑在更大规模上使用有风险的基因驱动来减少昆虫的痛苦而不带来任何人类利益。
那么关于机器智能可能不会在几个世纪内消除自然的论点呢?我认为地球上大部分生物生命在几个世纪内消失的可能性超过50%,所以为生物圈重新设计的长远未来规划在许多合理的未来情景中不会有回报。此外,如果几个世纪后生物仍然占主导地位,那么可能要么
- 文明已经崩溃,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将没有资源来实施快乐主义命令,或者
- 文明将比现在更先进,在这种情况下,重新设计生态系统对近未来的人类来说可能会容易得多,成本也会低得多。
减少无脊椎动物数量可能更有效
从我上面的评论可以看出,我对人类的无私和同情心持怀疑态度。依赖未来人类在大规模上做利他的事情的策略似乎不现实。即使是直接旨在以平凡、非高科技方式减少野生动物自然痛苦的广泛干预,在我看来也是相当不可能的。
相反,我怀疑我们可以通过引导现有的人类活动来最大程度地帮助野生动物,比如那些减少野生动物栖息地的活动。人类可能已经无意中通过减少野生动物数量而将地球上的总痛苦减少了~10%(?)。这可能比大多数HI项目希望实现的影响更大。
我赞成研究各种人类环境活动对野生动物痛苦的净影响,然后推动那些减少野生动物(特别是无脊椎动物)数量的活动。我们可以鼓励减少对栖息地保护和重新野化的投资,更多地强调创造就业而不是物种保护,以及扩大那些减少无脊椎动物数量的经济发展形式。例如,印度尼西亚破坏雨林的棕榈油生产通常被认为是减少贫困的重要途径(尽管我不完全确定棕榈油生产对昆虫痛苦的净影响)。
减少野生动物数量可以通过顺应人类自私的本性而不是与之对抗来实现。出于这个原因,减少数量似乎可能比开发昂贵的高科技解决方案更有影响力,作为一种防止动物在短期内遭受痛苦的方法,因为后者需要多年才能实现,而且人类没有自私的理由去部署。
HI对痛苦的关注很重要
正如在"引言"中暗示的那样,HI哲学的一个我认为确实有重大影响的方面是它对减少痛苦的关注。推广减苦伦理学在扩大整体减少痛苦运动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并将创造更多可以追求各种项目的活动家和思想家。考虑到HI信息所触及的人数,Pearce的工作在传播减少痛苦的价值观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
另见
与David Pearce关于这篇文章的讨论。